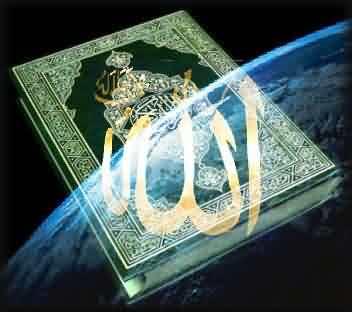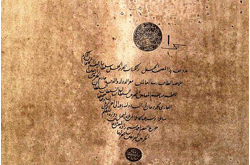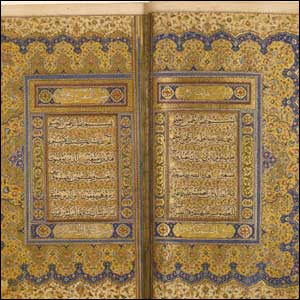粉红现象指的是天朝群众对统治集团的忠诚和顺从,他们无限热爱并忠于他们的领导,与它们永远保持高度的一致。这种现象波及十多亿百姓,包括为数不少的宗教信徒。
按理来说,宗教有固定的崇拜对象,有排他性的教义,有独自的经典,有特殊的教规,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为什么一些宗教信徒之中也有大量粉红存在,这方面比较严重的是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其中的粉红基数远远多于基督教和天主教。
几年前,我和李威逹律师一起在邢台认识了当地伊协的领导,他对今上的政策赞不绝口,让我们立即判定他是个粉红,李律师于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穆斯林笃信一神论,本该无限忠诚于安拉,却为什么其中的粉红却远远多于基督徒呢?
在我看来,其原因比较简单,这就是伊斯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本土化。伊斯兰传入汉地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异域宗教,为了在中国扎根生存,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在不违反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益的情况下适者生存。于是,伊斯兰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汉伊斯兰文化。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皇权崇拜,皇权高于人权,也高于教权,甚至高于佛权和神权,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一切外来宗教,以及宗教神祇,都要让位于皇权。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宣扬安拉至大尚且可以,但在公开的场合里,必须对圣上山呼万岁,否则就面临杀身之祸。首先做出调整的是佛教,佛教本来提倡众生平等,除了礼佛之外,没有理由对任何人躬身下拜,然而佛教高僧法果却主动给北魏太祖拓跋珪行礼,并且找出一个高大上的理由,他称太祖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武则天为了当上女皇而煞费苦心,在她的授意之下,一群高僧撰写了一部大云经,其中提到弥勒将以女身转世,还要“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过瘾,最终高僧法名又对这段经文进行注疏,直言转世的弥勒就是当今的天后娘娘。最终,武则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她也厚报了佛教,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很多佛寺佛塔和石窟。
伊斯兰教本是最彻底的一神论,“除安拉外,绝无神祇”,这就需要信徒只能对安拉保持绝对的忠诚和服从,而在中国,拜安拉而不拜圣上是不会得到容忍的,于是,穆斯林们就必须对教义做出一定的调整。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最终使伊斯兰教教义高度儒化。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复初等人既是一代经师,又是儒学大家,于是被人称为回儒。为了比附儒家四书五经,王岱舆著《清真大学》,马安礼译《天方诗经》,刘智著《天方三字经》,又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在《天方性理》中,刘智引入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们将“念礼斋课朝”比附“仁义礼智信”,还将古尔邦节解释为忠孝节。将穆圣称为西方圣人,而将孔子称为东方圣人,将圣人的弟子称为大贤,将穆圣的妻子称为圣宫。为了与中国的贞操观保持一致,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之中,还刻意将海迪洁嫁穆圣的时候说成是处女:“一,生为国女,不屑为官民之妇,二,才貌双绝,视通国无一堪配之人,三,巨富无对,未见一人有福力可受其业者,各国来聘皆不许,至是四十岁矣,仍然一闺阁处子。”(《清真大典》伊14-112)
他们将古兰经中要求对主事人的服从解释成对天子的服从,在刘智的《天方典礼》中,提出天道五功人道五典的概念,五典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在臣道中,他指出:“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故贤臣事君,无时无事不以心致之于君。”(《天方典礼》P136)在马注的《清真指南》之中,更直言“天之子,民之父,真主之真影,痛痒之所由关也。”(《清真指南》P214),伊斯兰教的礼拜,也被他解释为“穆民七日朝礼,登楼赞念,哀祈真主,求将尊大皇王永久,贵嗣永久……慈悯我皇王国土永久,公道加增”(《清真指南》P216)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可以给皇帝下拜,只是给皇帝下拜是额头着地,而给真主下拜则需要鼻尖着地。
他们这样做,还因为伊斯兰教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教合一史,为了维护哈里发的权威,他们曾将哈里发视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言人,什叶派更将他们的最高领袖奉为真主的迹象(阿亚图拉),直到现在,穆斯林国家还有周五为当地的苏丹祈祷的传统。既然穆斯林国家如此,那么中国的穆斯林们先贤们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对中国君主的服从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这样,“忠君孝亲”的概念被移植进了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之中,穆斯林们不知不觉地从对真主的一元忠诚改变为对真主和圣上的二元忠诚。也许正是这种教义的畸变,导致穆斯林们世世代代的皇权崇拜。他们永远忠于当朝圣上,即使被穆黑们长期诟病的清末回变,也是被迫无奈的起事,却从来没有推翻朝廷的念头,边打边降,等待着招安投诚。相比之下,作为信基督教的洪秀全,却整出了个太平天国,直言斩杀清妖,恢复太平。虽然他后来玩坏了自己,但从一个侧面来说,穆斯林对君王的忠诚的确是有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一些门宦的教主利用穆斯林的传统,恬不知耻地将中国的领导人称作“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一个阿訇在宣讲古兰经的时候,提到“服从真主和使者,以及你们中的主事人”,直言“主事人”就是中国某某裆。我当时对他那令人作呕的嘴脸大为惊愕,没想到几年之后,很多阿訇竟然开始同样的论调。阿訇基层尚且如此,一般群众亦步亦趋也就不足为奇了。
伊斯兰教之中有一种罪恶称为渎神罪,换言之就是多神崇拜。这个词的阿拉伯语为“什尔克”,中国穆斯林翻译为“举伴罪”或者“以物配主”,意为在真主之外崇拜其他人或物,这是古兰经提到的唯一不被饶恕的罪行。然而穆斯林们却只将多神崇拜保持在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他们的确能做到不向有形的偶像鞠躬叩头,然而在他们心中,在真主之外,却有另外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那就是当今圣上。他们将这群普通的皮囊上升到神明一般的位置,对他们由衷赞美,对他们感恩戴德,对待它们的政策,无论对错,永远地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甚至还会主动贯彻,坚决服从。虽然他们没有对那东西做“乃麻子”,但他们可以通过发朋友圈来表达他们的拳拳之心。
穆斯林们粉红多的第二个原因是认知有限,混淆了家国情怀与统治集团之间的区别。穆斯林群体之中流传着一句所谓的圣训“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句话中的“国”的原意为“窝巢、家园”,后来引申为“国土、祖国”。本来,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同胞,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一种正常的自然情感,但这句话不等同于热爱某个郑泉。穆圣热爱麦加,但并不意味着他热爱麦加的统治集团,穆萨热爱以色列人,但不热爱法老,耶稣热爱基督徒,但不热爱本丢彼拉多,谭嗣同热爱中华同胞,但不热爱慈禧太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祖国生生不息,而历朝历代只是暂时的存在。普通群众分不清祖国和郑泉的区别,再加上统治者别有用心的洗脑宣传,他们就混同了国和裆的区别,将爱国等同于热爱某个郑泉,在他们看来,裆国一体,不爱裆就是不爱国,这罪名可是非同小可。所以,粉红现象,只是他们的天真的粉红思维的自然流露,而且被他们视为天经地义,符合经训的正义之举,如果你敢有微词,他们马上就一幅维护正义的模样,将你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踢出他们的朋友圈。
另外,认知有限还体现在他们对历史的无知,由于他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画面,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之中,某个裆派领导他们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裆反动派,领导他们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这些千篇一律的教导,使他们忘记了饿死人斗死人的惨剧,忘记了谁不结扎房倒屋塌的悲剧,虽然那些灾难刚过去不久,然而本来一穷二白,现在有了一亩三分地,甚至能住上了楼房,开上了汽车,怎么能不对“英明的领导”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更何况,爱国在他们这里,有了教义的支持,早已成了圣人的教导,我们怎么能够违背圣意呢?再说了,爱国和爱真主并不矛盾,真主造化了我们,而龚缠裆领导我们得解放,所以我们感谢真主的造化,感谢裆的领导,这又有何不可呢?伊斯兰的一神论教义在他们这里,巧妙地从认主独一转变为忠裆爱国,而且还实现了逻辑自恰,不能不让人佩服。非但如此,穆斯林中还有很多人成为了裆员,尽管这个裆奉行无神论,其价值体系与伊斯兰格格不入,但穆斯林们在入裆宣誓的时候却可以出卖自己的信仰,信誓旦旦地高诵誓词,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中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了,很多人只是穆斯林后裔,对伊斯兰信仰一无所知,即使信教,也认识不到那入裆誓词对伊玛尼有着什么损害。
近年来,中国表面上看起来的发展壮大,也使穆斯林的粉红有了一定的底气。那年在巴基斯坦,一群穆斯林找到了一家能收到ccav的电视看春晚,大家边看边嘚瑟,“咱们国家那阅兵式,那阵势,有谁能比?” 于是,当他们看到被征用的农田上矗立起一座座高楼,当他们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战狼们的嚎叫,当他们在朋友圈看到“美国吓尿了,日本认怂了”之类的鸡血檄文,怎不会发自内心地喊出一句:“艾里哈姆杜,林我的锅!”(厉害了,我的锅)。此情此景,好像阿Q在鲁镇人面前炫耀城里人的繁华,不知不觉产生了共情,把城里人等同于自己了,对待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赵太爷抽他一个嘴巴子,然后厉声问他一句:“你也配姓赵?”
其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原因。按理说,爱一个人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他待你好你爱他,待你不好你还爱,那不是犯贱吗?然而,斯德哥尔摩患者却正是如此。在洛阳性奴案中,被关押在地下室的几个女孩子被迫充当案犯的性奴,失去人身自由,每天供他满足淫欲享乐,稍有不慎就被他暴打甚至杀害,但即使如此,她们却称呼这人为大哥,甚至爱上了大哥,主动讨好大哥,甚至成了大哥作恶的帮凶。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一座座清真寺的门前,飘扬着的一抹红色,那碧绿的圆顶与那一片血红相映成趣。然而,这种和谐的画面并不持久,接下来的是,一座座清真寺被枭首,一块块经文被毁坏,一个个阿校被关闭,孩子们被禁止信教,禁止踏入自己的父辈辛辛苦苦用乜贴盖起来的清真寺,这还是好的,在天山南北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所有听闻者都胆战心惊,悲愤有余。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粉红们跪舔的节奏,没有了绿圆顶,他们那一尘不染的白帽子在那血色之下仍然可以熠熠生辉。阿訇们被选为代表而进京开会,他们在朋友圈晒吃晒喝,晒裆的恩德,让他们住的是高级宾馆,与这些东西比起来,清真寺拆了又怎么样?阿校关了又怎么样?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解释,圆顶不是主命也不是圣行,拆了也不妨碍礼拜。孩子们不来清真寺也不要紧,毕竟学业重要。至于西边那事情,你最好少说两句,因为那是碰不得的红线。我理解他们的初衷,中国人对暴郑有着深刻的集体记忆,以至于每每提起来就会战战兢兢,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那真是吓大了的一代。好吧,你们可以集体噤声,但你们不能够再主动粉红吧?它们一边拆着,你一边赞着,它们一边抓着,你一边舔着,请问你是瞎了眼,还是良心喂了狗?
诚然,基督徒中也有粉红,基督教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历史上他们也在上帝的名称问题和祭孔问题上做出过妥协,他们也有爱国会和三自会,但相对来说,他们群体中的粉红基数要少得多,而且他们粉的同时不忘传教,转过来看看穆斯林们,我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总结一下,穆斯林中的粉红现象是因为高度的本土化,有意无意的本土化,造成了伊斯兰教义的畸变,而不知不觉受到了皇权崇拜或者国家崇拜的浸染,使粉红现象获得了一定的教义支持,加上穆斯林普遍的无知,情感的单一,以及对强权的恐惧,导致粉红现象严重,宗教的纯洁性因此受到了严重污染,不得不值得深刻反思。
这几天发生的辱圣事件,很多穆斯林都在跟风批判马克龙,似乎他是穆斯林的头号敌人,然而大家却忘了这位总统曾经访问西安的清真大寺,马良骥大阿訇还带他进了大殿,而大家更不知道的是,这位总统曾经在9月8日指控东边发生的事情是反人类的罪行。穆斯林们患有选择性失忆症,以至于热点周刊讽刺到,他们对法国兴师问罪,却在赵国面前成了哑巴。对于天山南北发生的悲剧,穆斯林乌麦的集体噤声,实在是一种耻辱。
某兄弟是千百个受害者之一,他如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个兄弟出于好意给我说,而你又好端端的,干嘛像他一样愤愤不平。我想他一定不知道那段圣训,“穆斯林是一个完整的躯体,当身上的某处器官疼痛,全身都会疼痛”,如果我们无视穆斯林同胞的苦难,那我们信仰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罪恶充耳不闻,那我们的良知何在?如果我们口口声声信奉真主,却又对被造物怀着深深的恐惧,那么到底算什么穆斯林?穆圣教导我们要说真话,哪怕真话是苦涩的。他提到真主最喜欢的七种人,其中有一种是在暴君面前敢于直言的人。扪心自问,在我们昧着良心做粉红的时候,我们配做真主喜欢的人吗?我们配做穆圣的乌麦吗?在我们抗议别人辱圣的同时,我们的懦夫行为,不是对圣人的宗教的一种辱没吗?
这篇文章不是让大家一定要起来反抗什么,而是让大家在乱世之中保持信仰的纯洁,当你无力改变什么的时候,你哪怕用心憎恶,而不是为了今世的蝇头之利而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我们很快都会离开尘世去见真主,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真主那里得到清算。
无花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穆圣诞辰
打赏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