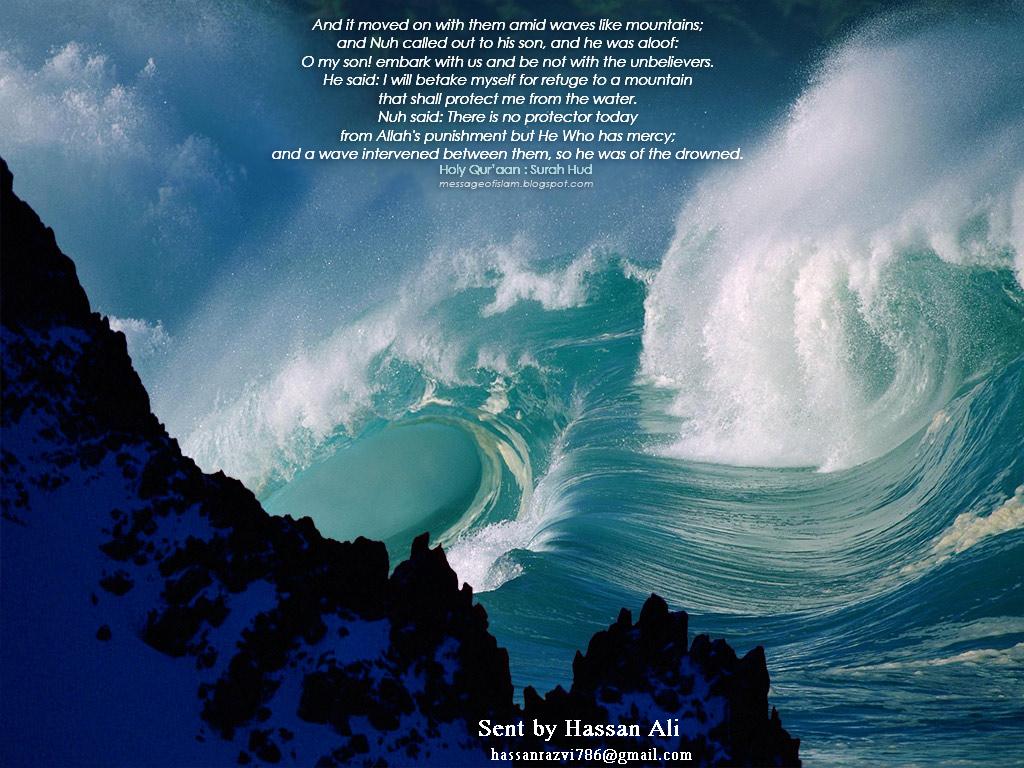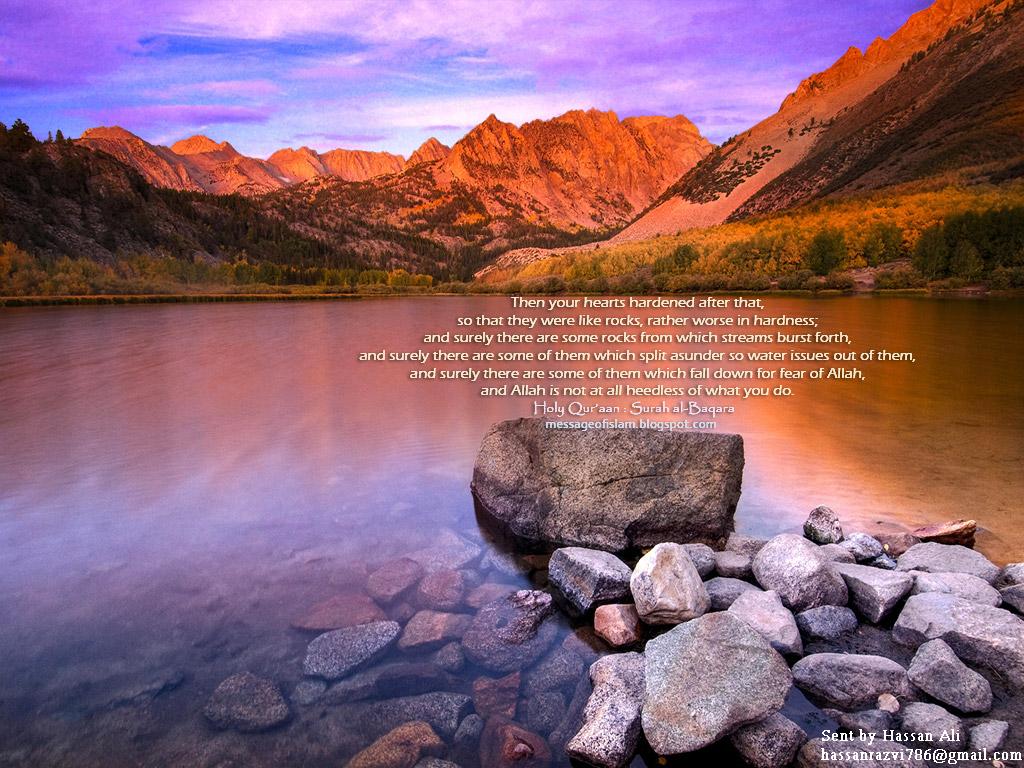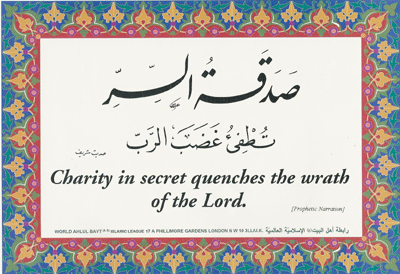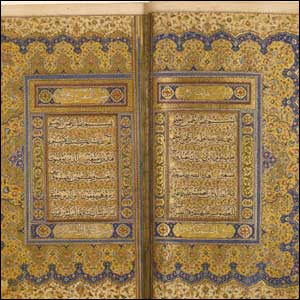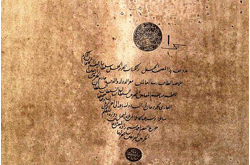在马来西亚过了几年不知道冬夏的日子,随着全面的解封,我于近日有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从吉隆坡起飞,转机新加坡,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全部旅程花费了24小时以上,可谓漫漫征途,不过这给呆在马来西亚两年多没有跨出国门的我,一次全新的体验。
聚礼之后,与前来送行的聪聪和小虎相聚在伊达曼的女王芭尓琪丝餐厅,聪聪点了三份羊肉,加一壶阿拉伯茶,每人外加一瓶芭尓必看,饱腹之后开始上路。一个小时到达了机场,我拎着行李箱办理登机手续。行李箱装了几件冬天的衣服,这是我前几天特地到HM买的,因为马来西亚天气炎热,我的衣柜里没有一件可以驱寒的衣服,临行才只得现买。另外给当地的朋友带了几本我的新书,加上马来西亚特产的白咖啡,就这样装了满满一大箱子。
值机人员看了我的核酸报告,以及申根签证,给我办理了全部的登机,顺利地出了马来西亚海关,我不禁在心里轻轻说了一声:别了,马来西亚。
进入候机厅,先找到苏绕做了礼拜,然后进入我要去的登机口,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离开了吉隆坡,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开始降落,俯瞰夜色之下的新加坡,灯火通明。马六甲海峡上,一艘艘船舶散布在平静的深蓝色的海面,像镶嵌着一颗颗明珠。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是一个很大的机场,我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首先找到了祈祷室,新加坡机场的祈祷室更大,供世界各地的旅客在这里停留,一个西方面孔的年轻人在里面祈祷,我摆上拜毯做了两拜之后,说了萨拉姆离开。
凌晨将近一点,开始登机,我乘坐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客飞机,由于没有强调座位,我被安排在了中间位置,两边有人,这样出来进去不太方便,但我这个人也不爱给人添麻烦,只是这座位对于我的体格来说是有点挤了,出行毕竟没有家里舒服。飞上高空之后开始吃饭,新航的饭食还算不错,鸡肉和鱼肉两种,我理所当然的选择了鸡肉米饭,然后又喝了一杯果汁,吃完不久困意袭来,我就半躺着睡了起来,但由于座位不舒服,我开始腰酸,就这样翻来侧去,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按照平时的时间已是清晨,但由于飞机要跨越六个时区,还有六七个小时才到天亮。我的生物钟肯定不适应,在接下来的六七个小时里,我就打开平板开始看书,看的是我提前下载的傅志彬先生的《洗脑的历史》,书写得风趣幽默,我不知不觉看了七八章,就这样度过了漫长而无聊的空中旅程。这一天的晨礼比平时推迟了六个多小时,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窗外的天幕才开始泛蓝,眼看着一抹朝霞出现在天边,飞机降落在德国慕尼黑国际机场。此次飞行相对平稳,很少有颠簸,但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机舱里的全体旅客还是响起了掌声。
东航的空难还在调查之中,生命无常,所以每次平安到达,都是一种万幸。一路上,我飞越了印度的阿姆利则,飞越了伊朗的马什哈德,飞越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飞越了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要知道下方正炮火隆隆,普京发起的入侵正造成数千平民的丧生,我祈祷真主早日毁灭这个恶魔,以及它的徒子徒孙,如果不是牠们,无辜的人民怎能遭受那么多苦难。
走出飞机,我呼吸到了清凉的空气,感赞真主,使我再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早晨的慕尼黑机场,已经人来人往,亚洲面孔顿时少了很多。然而这块土地我们并不陌生,不光是因为慕尼黑的啤酒,还有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二战,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一个恶魔的疯狂而死于非命。临行前一天,我还看了一部记录波兰犹太人悲惨命运的电影《钢琴家》,那些本来可以体面地生活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颠沛流离的难民,失去财产,继而被成群结队驱赶到集中营,一批一批杀害。这不禁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民族,他们的苦难让我感同身受。我们与德国的渊源还不止于此。诞生在德国的犹太人老马,被东方大国奉为教主,结果带来了连绵不断的灾难,中国人民付出了亿万生灵的代价,然而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逃出生天。
德国人民有幸摆脱了两大恶魔,所以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但我也不能苦大仇深,毕竟我们的苦难终有到头之日,我相信此次侵乌,普京政权必将走向衰亡,接下来如果他的干儿子有样学样,离终结的日子也不会太远。我常常给陷于忧愁的朋友说,熬着吧,正常的情况下,以我们的生理年龄来看,应该都能熬过那一头家畜,熬过牠,你就是胜利者。
慕尼黑这里还是冬天,我买的冬衣有了用场,但候机厅里温暖如春,我发现了一个祈祷室,这个祈祷室门口的牌子上画着新月、十字架、六角星,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的几种标志,这意味着各宗教信徒都可以在其中祈祷,就凭这一点就早已领先大国一个世纪。十多年前我去北京机场,由于国际压力,搞了个所谓的冥想室,一两米平房的空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敢叫祈祷室,生怕这祈祷二字让人联想到了宗教。另外,昆明机场、西安机场也有模有样搞了个祈祷室,但没过多久,由于习五一这群民粹的叫嚣,又被当地悄悄地撤销了。
整个欧洲都是近亲,无论法语德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无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都属于欧罗巴人,从外形上极难分辨。但好在欧洲没有大一统思想,所以分成了若干个小国,才不至于一损俱损,他们各自享受着各自的民主自由,再也不受大国铁蹄的欺压。
欧洲腹地群山环抱,远处的山峦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大地上绿草茵茵,分布着一个个宁静的村庄,这场景我们曾在影视上见过多次,今天我又亲眼目睹。下了飞机,领了行李,很快走出机场,这里没有繁杂的海关入境手续,人们凭着申根签证,可以到访欧洲各国,所以方便了很多。
机场外阳光和煦,并没有想象中的寒冷,路上车辆也不多,行人也不多,感觉格外地宁静。在这里问路,随便哪个人都会异常热情的给你指路,所以即使手机没有网络,也不会为迷路而犯愁。经过了几天的逗留,我也渐渐熟悉了当地的地理。
朝阳初升,寒气逼人,行人稀少,路边的小公园里,静得可以听到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一阵子嘣嘣嘣的声音,让我意识到了那是啄木鸟在啄着树干,一位大叔出来遛狗,看见我之后给我一个温暖的笑容。
在市区的交通,通常是坐有轨电车,我喜欢这种感觉,跟随着满车的乘客,缓缓前往我的目的地。电车穿过静静的河流,穿过小花园,花园里鲜花怒放,一树一树的梨花,宣示着春天的到来。
闲暇之余,我会漫步穿行在古老的城区,街两边到处是古老的房子,典型的欧洲建筑,大多用巨石建成,少说也有上百年历史,记载着厚重的历史。
这里的教堂很多,但教堂里人并不多,闹市区总有教堂,供繁忙的人们坐下来休息祈祷,远离尘世的喧嚣,让心灵宁静,这就是有信仰的社会的特点。
街道上,时而会见到几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士,看长相应该是阿拉伯人,他们来到西方定居,享受着这里的自由空气。相比巴勒斯坦的同胞,他们肯定是幸运者。人群中不时见到非洲裔人士,他们应该也是很早就移民到这里的,欧洲一直有黑人居住,这大概是地缘接近的原因吧。如果你住在欧洲的附近,能够很容易地迁徙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也会移步于此,因为这舒适的环境,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路过一个小广场,一些人坐在凳子上喝咖啡,一群鸽子在地上啄食。我发现地上并没有鸽子粮,它们忙碌不停地啄食的只有细微的小石子,这东西没有影响,充其量能填满嗉子,还有什么比吃土更令人沮丧的事情吗?但鸽子们却咕咕地欢唱,这世上的物种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这里也有清真寺,所以我很快找到了清真寺的所在位置。清真寺里陆续有宾客进来,我进去之后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表示要先悟杜(小净),再去礼拜。悟杜可以洗去一身的疲惫,让人顿时神清气爽,洗完之后来到大殿里,站在真主的面前倾诉一番,是我此刻最想要做的事情。随时纪念真主,我喜欢享受这样的宁静。赤脚踩在柔软的猩红色地毯上,面向东南方抬手入拜。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了东方大陆,来到了西方世界,但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真主护佑着亚细亚人,也护佑着欧罗巴人。我喜欢在跪坐的时候说出我的愿望,这是我和真主的秘密,他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坚信我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出了大殿,与几位阿富汗人士寒暄了几句,他们没有塔利班统治下的大胡子,一身西方的装束,几位女士也是在走进清真寺的时候才戴上了头巾,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曾经在巴基斯坦见到的阿富汗人,男人戴着毡帽,而女人则穿着从头蒙到脚的斗篷,即使面部也被蒙在纱网里,这种装束在古兰经中并无规定,却被当成制度一般的奉行。如果你看过电影《追风筝的人》,就一定会明白为什么那个移民美国的阿富汗青年,费尽千辛万苦一定要把自己的侄子弄出来的原因了。高压统治之下,人人不得安宁,最近传出塔利班又开始禁止女童上学的消息,这不禁让人痛心,本来伊斯兰教要求男女均有学习的天职,而自诩奉行教法的塔利班却禁止女童学习文化。前几天,伊斯兰国家组织召开会议,竟然请了一位正在消灭伊斯兰文化的王太监参会,这真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可见这些穆斯林国家的领袖们已经无耻到何种地步。
离开了清真寺,我坐公交返回驻地,回到房间里,躺床上小憩,关注一下油管和推特,得知普京宣布想要停战,我知道西方的联手让他已经招架不住,想顺坡下驴,草草收场,但我想即使他愿意停战,乌克兰也应该乘胜追击,让这罪恶的战争罪犯尝到应有的刑罚。
有一天的晚餐,我和几位朋友在酒店附近一家印度餐馆就餐。印度菜是我的所爱,打开菜谱我架轻就巧,点了经典的布尔雅尼(羊肉咖喱饭),以及一壶迦叶(奶茶),在马来西亚,迦叶已经换成了马来语的提塔雷,但现在我如果说提塔雷,这德国印度人未必知道啥意思,所以我说了印地语的词汇,服务生微微摆头,表示OK。我了解他们这熟悉的动作,因为印度人的摆头表示同意,而不是点头。有几位朋友是第一次吃印度饭,却受不了咖喱的辣味。对面的两位英国姑娘一个表示想喝我的奶茶,另一位说她去过拉合尔和卡拉奇,她像我一样热爱印度(以及巴基斯坦)。
餐桌上,我们谈到了开封,我说开封是中国唯一还有犹太人的城市,犹太人被称为蓝帽回回,他们的教堂也叫清真寺,他们表示相当惊讶。我们谈到撒拉尔,我说撒拉人基本上都姓韩,而这韩是韩国的韩,其来源却是大汗的汗。我们谈到了铁链女,我说结婚证那位打眼一看就不是一个人,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牠们真当我们是眼瞎了吗?旁边一位朋友说,这叫“我悄悄地蒙上了你的眼睛”……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已是晚上八点多。而此时的马来西亚,已经是夜里的两点多了,为了照顾我的时差,大家结束了聚会,我也回到驻地休息。
这里的夜晚也非常迷人,河畔灯火辉煌,天空中下起了小雨,但却感觉不到寒冷,这里已经放开了口罩令,人们已经学会了与病毒共存,由于有效疫苗的普及,奥密克戎已经没有太大的威力,欧洲已经将新冠当做地方流行病对待,所以街头已经很少有人戴口罩了。反观东方大国,虽然十多亿人都被迫打了疫苗,但由于国产疫苗的无效,病毒仍然在肆意蔓延,束手无策的当局只有无休止的核酸、封城、动态清零,三板斧砍来砍去,让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初大国让全世界抄作业,现在全世界都毕业了,大国还在艰难地做题。
欧洲的多个国家之间可以自由往来,凭申根签证可以轻松从一国到达另外一国,或坐火车或自驾游,都非常方便。就这样我在几国之间逗留了数日。旅行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紧张而忙碌,所以其间的几日我没有留下文字的记录。
告别的日子到了,本来要结束此次旅行,却由于转机的原因,使我此次旅行有了意外的收获。由于前往马来西亚的航班是隔日才有,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中转地逗留两天一夜,就这样,我意外地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荷兰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端,毗邻大西洋,紧接着北欧,属于苦寒之地。出了机场,迎面是刺骨的寒风,天上还漂着雪花,我庆幸自己临出门的时候把行李箱里的棉马甲取出来穿上了,所以还不算冷,只是腿上这条绒裤就显得太过单薄了,寒气直透,冻得我哆嗦。出境没有任何手续,申根签证的各国可以自由往来。只是在出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插曲,当我对着机场大厅拍照的时候,走过来两个警察,对我一顿询问,问我为什么拍照,问我什么工作,我说我是学生,他竟然调侃我一句,“so you are a small guy”(这么说你是个小毛孩!)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胆大啊。找了个售票机乱点一通,买了一张火车票跟着大家上了火车,哪知道火车路线和我设定的酒店位置不同,却越走越远,我只有将错就错,改变行程,来到了市中心的火车站。
火车站里没有想象中的温暖,尤其是大厅的穿堂风,更是让我倍受摧残。出来找车,却发现没了wifi之后却无法导航,本来我已关闭了国际漫游,到了这里之后还需要重新开通。打开APP一阵操作,总也不得要领,还必须打电话给马来西亚的客服,向她表达了我的意愿,要求人工开通漫游。她揣着明白装糊涂,非要问我哪个号码,这还用说吗?我也记不住。报了号码之后,又要问我哪个国家,我报了几遍她都听不清楚,非要问我怎么拼来着,难道是我发音有问题吗?这里说明一点,荷兰的英语发音其实更接近“尼德兰”,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词都是生疏的,这也难怪这位女士了。很多女士地理不好,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印度的时候,一位女士热情地联系我,说她那里有朋友,给我发来地址,原来是印度尼西亚。
折腾了半天总算开通了漫游,我查了公交车,却不在北广场而在南广场。我只有面对北广场的湖面,听着游轮的汽笛声望洋兴叹,叹过气之后穿过大厅来到南广场,没想到出门却是别有洞天。南广场明显通着城区,一出门就望见一幅浪漫的画卷。广场四周一座座色彩不一的欧洲建筑,参差不齐的尖顶,五花八门的纹饰,运河上缓缓而行的航船,远处高耸的教堂,回过头来再看火车站,也是一栋如城堡般的建筑,正中央有两面大钟。街道上不时驶过来有轨电车,遇到行人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铃铛声。我被这美丽的画面陶醉了,当即决定步行游览城区。
首先跨过一座大桥,来到了著名的圣尼各老教堂,这应该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为华丽壮观的教堂了,教堂里的穹顶有精美的壁画,四周也有描述耶稣生平的壁画,正中央的圆形穹顶有细致而繁复的花纹,以及环绕着穹顶的彩色玻璃窗。教堂正前方也是玻璃窗彩画,中间的祭坛处有一个巨大的王冠。右边的侧厅有耶稣受难像,左侧也有对应的雕像。这个教堂可以容纳几百人,虽然不大,但足够壮观,游人们都在静静地欣赏,有信徒们坐在长条凳上祈祷。我在出口处的善款箱里投进去了个一个五欧元的硬币,然后轻轻离去。
离开教堂,迎着寒风在河边行走,跨过大桥就来到了达姆拉克大街。街道上的各式建筑实在是令人倾倒,我拿出手机一阵狂拍,以至于我都来不及欣赏这梦幻般的画面了。阿姆斯特丹是个水城,密密麻麻的运河贯穿全城,人们可以坐渡船游览城中的美景。在街上行走不远,就发现有一家印度餐厅,写着“Halal Food”,决定走进去吃饭,一是借食物的热量暖暖身子,二是希望能给手机充电,因为手机几个小时的折腾,电量已经告急。走进去发现没有什么印度餐,更像是土耳其餐,我点了个沙威尔玛,把配套的可乐换成了热茶,没有可以充电的地方,不过好歹可以暖和一下了。吃完饭浑身暖和起来,接着前行。
大街上游人如织,不远处有一个类似埃及石柱的纪念碑,原来这是阵亡将士纪念碑,对面喧闹起来,我回头看见一座庞大巍峨的建筑出现在眼前。这是阿姆斯特丹的皇宫所在地。这座皇宫的规模秒杀故宫太和殿,无敌地耸立着,诉说着它不可撼动的地位。皇宫的广场上成群的鸽子在飞来飞去,人们都忍不住拍照留影。这座皇宫建于荷兰王国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荷兰是地球上的霸主,除了欧洲本土之外,在加勒比海等地也有大量的殖民地,甚至整个印度尼西亚都是荷兰的领土,阿姆斯特丹也当仁不让地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以至于起初的纽约也归荷兰所有,纽约的原名就叫阿姆斯特丹。熟悉地理的人应该知道,在美洲大陆上有不少地方与欧洲的城市同名,这就是殖民者留下的痕迹。
皇宫的北侧有一座新教教堂,我随着游人鱼贯而入,却被告知要买门票,说这不止是一座教堂,而是一座博物馆。新教教堂没有天主教堂的华丽,也没有珍贵的壁画和雕塑,所以我果断放弃了参观,出来后准备去梵高美术馆,我知道参观需要预约,但又想碰碰运气,看不成先认认地方也行。看导航步行需要十五分钟,哪知道这棋盘般的街道,拐来拐去实在难找。坐公交怕太麻烦,没想到却差点跑断了腿。好在总算是找到了地方,远远地看见河对岸一座古红色的建筑,又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看地图确定这不是梵高美术馆,而是荷兰国立博物馆。国立博物馆有高大的门楼,穿过去之后是一个广场,广场对面才是梵高美术馆。找个地方坐下来在网上购票,哪知道最早的票也在四月五日,看来我注定要留下遗憾了。之前曾经和友人相约有机会一起来看梵高的画,不知道是否是她下了蛊,所以我此次独行才未能如愿。当下决定参观国立博物馆,以弥补梵高美术馆的缺憾。在网上订了当日的票,趁邮件没有发来的时候,到梵高美术馆门前拍张照片望梅止渴,又进入旁边的纪念品商店逛了逛,这时候也已经收到了参观码,于是返回国立博物馆进入参观。
多亏我有先见之明,带着充电宝给手机续命,所以才让我如此从容地参观,只是没想到时间还是不够用,从三点参观到五点闭馆,两个小时时间,三层楼几十个展厅,根本不可能仔细观赏,所以我只能有所取舍,遇到普通的展品就走马观花,遇到珍藏的展品就多多停留。一楼的宗教艺术吸引了我,大量有关基督教的世界名画,之前只是在网上或者画册上见过,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真品。除了油画,还有不少木雕石雕,个个也都精致无比,有童贞女玛利亚怀抱耶稣的,有最后的晚餐的,有从十字架上解下的耶稣,有五饼二鱼,还有与众使徒进入耶路撒冷的,耳熟能详的宗教故事被艺术大师们用精巧的画笔和刻刀表述了出来,真是让人赞叹。
接下来的展厅有大量的航船模型,还有很多枪炮,荷兰人就是仗着船坚炮利开创了他们的领地,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各领域的发展,无论建筑、航海、武器,还是音乐、瓷器,在这里我见到了荷兰产的精美的瓷器,当然也有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其中有中国的青花瓷,还有伊朗的玻璃器皿。有个展厅陈列着大量的大量乐器,还有几架古老的钢琴,西方人在这方面领先了中国几个世纪。
三楼是二十世纪的展厅,有大量的世界名画,包括维米尔、伦勃朗、弗兰斯·哈尔斯、扬·斯丁的杰作。其中有《倒牛奶的女仆》和《夜巡》最为著名,由于时间仓促,我最终没有找到《倒牛奶的女仆》,但却看到了那张巨幅的《夜巡》,为首的军官表情似乎有些仓皇,他带领的队伍每个人也有不同的表情,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然还有梵高的作品,可谓镇馆之宝,遗憾的是我都没有找到。广播里传来即将闭馆的通知,我遗憾时间太短,只有不舍而别。临别我发现了一个展厅,那是一个著名的图书馆,通体环绕着书架,有两层楼至高,书架上陈列着大量的藏书,荷兰人热爱读书的精神在此可见一斑。
出了博物馆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我再也跑不动了,只有按着导航坐电车回酒店,这里的公交上车买票,不过售票员告诉我,这票还可以继续使用,不知道她卖给我的是一天的还是两天的,因为刷卡我没记住数额。
总算来到了酒店,我的两脚已经肿胀,甩掉了脚上的鞋子,洗漱礼拜,然后直接钻进被窝,就这样一睡几个小时,才算是缓过来劲。明天还有一天时间逗留,我必须养好精神保持活力,才能投入新的战斗。
我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想起来还没有吃晚餐,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餐馆也都已打烊,阿姆斯特丹的夜晚是宁静的,找不到可以吃宵夜的地方,我出去溜达了一圈,冻得发抖,赶紧回来钻进被窝。翻看了一会儿微信,发现沙特已经传来见月的消息,而马来西亚则宣布未见新月而后天封斋。大部分国人唯沙特马首是瞻,所以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封斋,而我目前属于马来西亚的定居者,按照惯例我打算跟随当地。所以,对于我来说,斋月还没有到来,但朋友圈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祝福了,所以此刻我也该恭祝全天下的穆斯林朋友斋月大吉。只是今年的斋月第一天,我没有在东方,而是来到了西方世界,身处欧洲的最西端,在大西洋东岸上的阿姆斯特丹。
第二天的时间是充裕的,所以我早上不着急出门,八点钟的时候下楼吃早餐,酒店准备的自助餐还算丰富,由于不能吃肉(怀疑是猪肉),我只有吃面包、蛋糕、鸡蛋、牛奶、酸奶、水果,其实一样吃一点的话,这也不算少了,我喜欢把芝士夹在两片面包里做成三明治,然后辅以牛奶和咖啡,吃得饱饱的又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刷手机,之所以选择晚点出门,是因为有头一天的教训,在寒风中度过一整天确实不是滋味。所以我一直磨蹭到了十二点,洗漱完毕退房出门。按照原有的计划,我先坐12路电车去法提赫清真大寺。这里的公交非常便利,每次都有座位,我靠窗坐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车辆穿行在古老的街道,跨过一道又一道运河,有时候车辆就行驶在运河岸边,运河里不时有船舶经过。远处的天空湛蓝,街道上的建筑让人目不暇接,我多希望有朝一日带着亲友一起重游这美丽的城市。
法提赫清真寺(Faith Foundation)不仅是一座清真寺,还是一个伊斯兰中心,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有着两座哥特式的尖顶,棕红色的墙砖,从外表看不出像一个清真寺,只有顶部的一弯新月让我肯定了我的判断。清真寺从侧门进入,通过狭长的过道,方可进入大殿。我先去悟杜,沐浴室有一位白人老者,我向他说了萨拉姆,他礼貌地回敬了我。这时候还不到晌礼时间,寺里的礼拜者零零星星。旁边的侧厅里似乎有人在聊天,我洗好之后进入大殿。大殿是圆拱形的建筑,一个个小型的穹顶错落有致,大殿狭长,顶部有一扇扇细长的彩色玻璃窗。这建筑和教堂相似,查看了资料,果然这里曾是一座教堂。1979年,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穆斯林买下了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教堂原本的末尾部分改为米哈拉卜(朝向壁龛),镶嵌了精美的瓷砖,瓷砖上烧制着古兰经宝座经文环绕着拱门。而顶部的墙面,则用深色的墙砖镶嵌了两个正反对称的“安拉”字样,顶部悬挂着几盏巨大的吊灯,地板上铺着猩红色的地毯。这色调古朴而庄重,让人肃然起敬。我站在殿里做了两拜,之后便倚着石柱休息。这场景让我想到了伊朗设拉子的粉红清真寺,而这座清真寺的墙砖和花窗与粉红清真寺有些相似,只不过那座是专门的清真寺,而这座却是由教堂改建而成。如果进一步了解,其实在欧洲由教堂改做清真寺的先例并不算少。此消彼长,基督教没落之后,穆斯林却增加了,这种静悄悄地变迁,多年以后也许会再次改写欧洲的格局。
离开了清真寺,我漫步向前,不远处便是高耸的西教堂的钟楼,这座钟楼顶部有一个小小的圆拱顶,看起来更像一座清真寺的尖塔,然而这却是一座真实的教堂。教堂内部没有华丽的装饰,也没有什么雕像,直觉判断这是新教教堂,教堂的正前方没有讲台,只有一面巨幅的风景画。而讲道的位置却布置在侧面,教堂的后方有着巨大的管风琴,顶部有大理石雕刻的耶稣头像。
教堂向北,是安妮弗兰克的故居,据说二战时期她藏身于此,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很多游人聚集在这里,然而今天却不开放。安妮故居门前临着运河,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很多游人在等待坐船。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水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然而对于同样生长在水城的我来说,坐船并不稀奇,所以我就继续沿街前行,到我的下一站目的地。
走了不远就到了荷兰的皇宫,皇宫昨天来过,只不过是在皇宫的正面,而今天我走的却是皇宫的后面,巨大的建筑遮住了阳光,走在建筑的阴影里有些寒冷,这时候又飘起了雪花,雪下得不大,但对于生活在热带三年多的我,还是有些惊喜。可惜的是,雪下了不大一会儿就停了,皇宫广场上又恢复了艳阳天。有个鼓手在拍打着手鼓,还有个小伙子装扮成加勒比海盗,不远处还有一位老人在发表演说,他的推车前摆放着很多巴勒斯坦的图片,还插着三面巴勒斯坦国旗。在遥远的西方仍然有人支持着巴勒斯坦的抗争,这老人实在让人敬佩。
皇宫南边是杜莎夫人蜡像馆,我花了25欧元购买了门票,准备进去长一长见识。这座蜡像馆大概有四五层,但每层的空间并不大,通过曲折的楼梯上去,里面的蜡像不少,与真人一般大小,而且栩栩如生,只是很多人物我并不认识,因为大多数蜡像人物都是西方的影视明星,我所知道的能看得出来的也就是钢铁人、蜘蛛侠、卓别林、复仇者联盟上的绿巨人等,其他都比较陌生。比较有名的历史人物倒是有甘地、达赖、爱因斯坦等人,政界人物有英国女王、奥巴马、川普等人,很多人与蜡像合影留念,我只拣了几个感兴趣的人物合了个影,比如梵高。蜡像馆的顶楼有一扇圆形玻璃窗,透过窗子就能看见皇宫以及不远处的街景。
从蜡像馆出来,准备再去梵高美术馆碰碰运气,反正我买的公交票是24小时有效,如果乘坐次数太少就不划算了,所以就当欣赏一路的风景。来到梵高美术馆,再次确认没有票,只有扫兴而归。地图上发现了一个性博物馆,于是就按图索骥,坐公交来到了那里。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楼,里面有三四层,陈列着不同时期的各种露骨的雕塑、照片以及美术作品,向人们展示着不同时期人们的性观念,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中国古代的展览,其中三寸金莲的绣花鞋是个亮点。东方以这种畸形的嗜好而闻名于世,至于西方我想莫过于贞操锁了,果然在楼梯的过道处,我见到了两个贞操锁的实物,用皮革和钢铁制成,关键部位只留一条缝隙,缝隙边缘是向外延伸的锯齿,这种产物标志着曾经的西方对女性的禁锢和压制,表明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而且为了保证这种附属品永远只为自己所有,不是通过爱和信任,而是通过一道锁子来实现,好在这是几百年前的产物,而东方大国至今还有人把女性当做可以买卖的商品,而且买回来还要用铁链锁住,以防她逃逸或者被别人占有。
下午五点多,我已经饥肠辘辘,不过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找到清真餐厅,我找了一家克巴布,老板是一位阿拉伯人,于是我同他讲阿拉伯语,听他的口音像是埃及人,我没有细问,只要了一个羊肉鸡肉混合的克巴布,又要了一杯阿拉伯茶。由于已经是斋月,我向他祝贺了“莱麦丹·卡瑞姆”(斋月大吉),他回复了我,我说你斋戒了吗?他回答说:“感赞真主”。我说我是旅行者,今天不封斋,他说欢迎你的到来。得知我是穆斯林,他向我询问中国穆斯林的情况,有多少人,都能斋戒礼拜吗?我回答说有两千万,有四万多座清真寺,现在被拆得剩下两万多座,其中一万多座被强制整改,拆毁了圆顶。公职人员、学生和儿童禁止斋戒礼拜,其他人目前还可以,但这是在内地,至于在棉花地则另有实情。(此处省略若干字)他听了之后一声哀叹,对我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我希望他在斋月为我们祈祷,他说一定如此。
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到了,傍晚我坐火车来到了机场。安检十分顺利,出境处盖了个章子,就算是可以离开欧洲了,然而在候机厅,前往马来西亚的航班却要另行检查,除了此前要求的核酸报告之外,必须把手机上的马来西亚疫情专用软件更新资料,上传核酸报告的截图,并且签署责任保证。就这样又折腾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可以进入前往吉隆坡的登机口了。这趟航班有两个目的地,一是吉隆坡,二是新加坡,看来往亚洲远行一次不容易,一趟航班把两个坡都涵盖了。
候机厅里有不少亚洲面孔,还有一些戴着头巾的女士,这应该都是前往此二坡的乘客。天色将晚,七点多钟,飞机缓缓驶入跑道,飞向蓝天,俯视着舷窗之外的阿姆斯特丹,我顺利地告别了欧洲大陆。
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缓缓降落,却发现第一站不是吉隆坡,而是新加坡,我只得在新加坡稍事逗留,本想不下飞机,却被告知必须离开飞机,到机场转悠一圈。新加坡的旅客已经纷纷离去,剩下前往吉隆坡的旅客按照要求再次来到一个区域,再次安检,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往马来西亚需要这么严格,就这样又耗费了一个小时,重新登机,前往吉隆坡。
大概四十分钟,飞机平稳降落在此行的目的地,我愉快地走出机舱,跟随人流一起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海关还算顺利,排队大概半个小时,终于走出机场,前来迎接我的聪聪已经到达机场门口,远远地向我招手。这是一股热浪袭来,我意识到已经从寒带来到了热带,坐在车里,我脱去了身上的绒衣,换上了半袖T恤,顿时恢复了热带模式。聪聪问想吃什么,我此时归心似箭,只想赶紧回到住所,做一顿可口的中国餐,于是他不再强求,将我送到了家门口,就此告别。我终于结束了此次收获满满的欧洲之行,平安顺利地返回家中。
老无
2022/4/12
打赏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