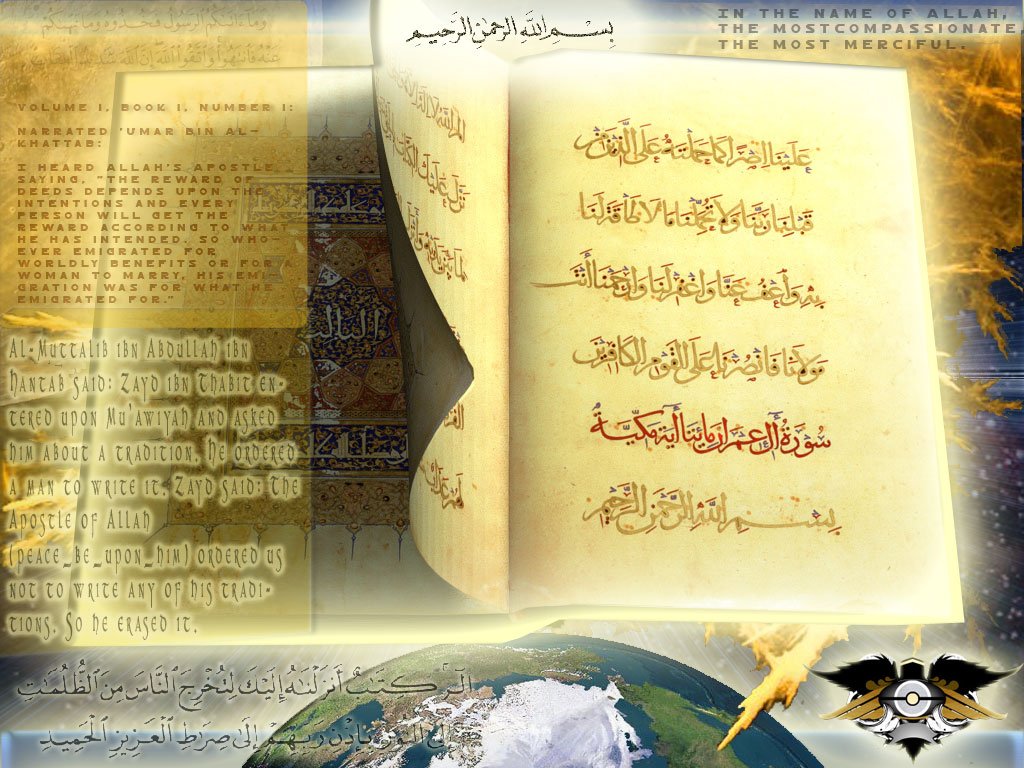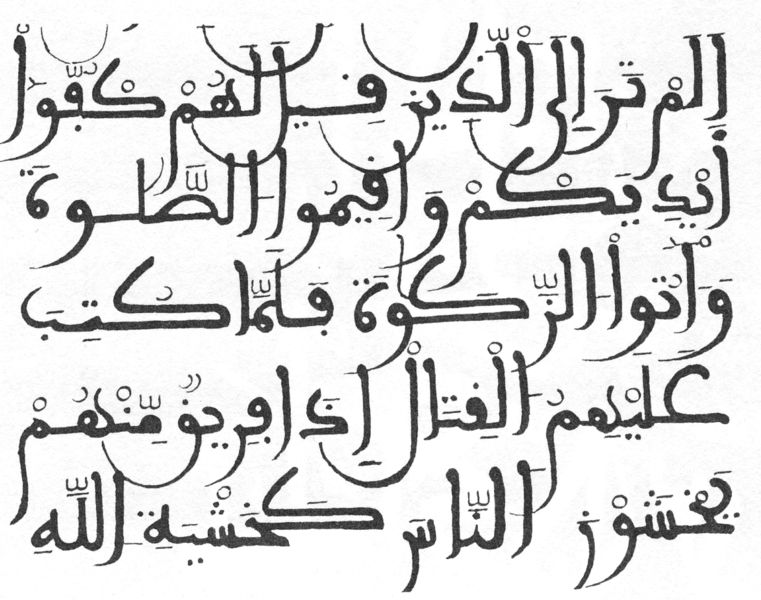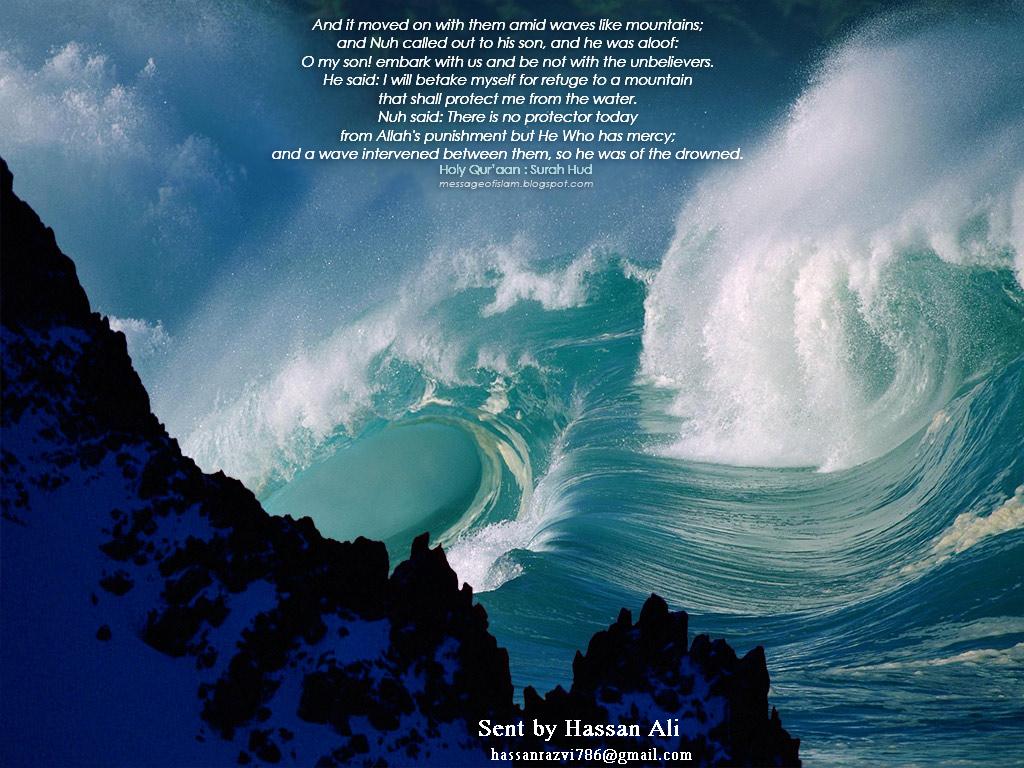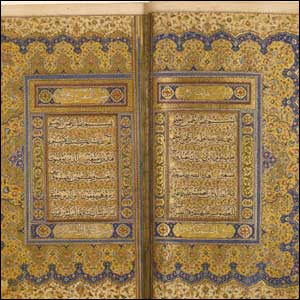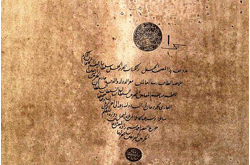今天看到一条朋友圈,一个穆女说老爷子喜欢吃壮壮的羊肉,所以今天的抓饭壮肉多,待我看图的时候,才发现她所谓的壮肉,其实就是肥肉。
但是,在西北某些地区,穆斯林是忌讳说“肥”字的,大抵是一说肥肉,就立刻能联想到猪身上那层厚厚的肥油吧,所以他们要改成“壮”字,照这样的逻辑,减肥产品岂不是也得说成“减壮产品”了呢?
你还别笑,类似这样的禁忌还真不少,到了云南,吃牛肉要说吃牛菜,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肉字特指猪肉,但如果你照此援例,把牛肉面改称牛菜面,把涮羊肉改称涮羊菜,把肌肉注射改称肌菜注射,他们估计会立即把你菜一顿。
到了河南一些地方,壮和肉都不忌讳了,但却有另一番讲究。某些地区,买肉要说割肉,馄饨要说荷叶面、元宝汤,但在西安,馄饨却还是馄饨,饮食名称与别人没有太多的区别,但当地回民忌讳说死字,一个人去世了,要说“殁”了,或者说“无常”了。
我自幼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语言行为都被教导,要有意识的和别人保持区别,我们不能说“灵魂”,要说“罗哈”,我们不能说爱吃甜的,要说爱吃咸的,因为据说甜的代指猪肉,咸的代指羊肉,一些回民甚至因此自称“盐丁儿。
有的人爱拿民族说事,以上述种种语言禁忌,企图证明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和汉人迥然有别。其实,上述所有词汇也都是汉语,即使与普通汉人的用法不同,也只是在同一种语言里刻意制造区别,不能说有了这种区别,就成了两个民族。陕西人把孩子叫娃,河南人把娃叫孩子,陕西人把姑娘叫女子,河南人把姑娘叫闺女,难道以此就可以分成陕西族和河南族?
况且,河南回民、陕西回民、云南回民的语言禁忌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只在当地有效。陕西回民死了要说殁了,河南回民却不以为然。宁夏人吃肥肉要说吃壮肉,陕西回民也不以为然。如果以语言差别断定民族,那么陕西回民与河南回民一定不是一族,否则为啥一个吃馄饨,一个吃荷叶面呢?
其实他们都是一族,只不过由于地域的封闭性,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形成彼此不同的忌讳。这些忌讳不是因为民族不同而产生,恰恰相反,相同的民族,也会由于各种原因形成千差万别的语言习惯。
究其原因,这些特殊的禁忌与民族无关,而与宗教有关。大家都是汉人,但一部分汉人信了教,从生活习惯上、语言习惯上,便会多多少少与其他汉人产生区别。例如汉人信了佛教,便不能杀生,不能吃肉,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要说阿弥陀佛。汉人信了基督教,便不能拜佛,不能烧纸,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要说哈利路亚。同理,汉人信了回教,便不能拜偶像,不能搞迷信,有了好事不说谢天谢地,要说知感安拉。
宗教使然,信教群体与普通群众语言上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往往只在宗教禁忌范围之内,宗教没有禁止的,则可以继续沿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徒、基督徒、穆斯林仍然继续在使用汉语,而他们的汉语与普通汉人群众的汉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宗教禁止吃猪肉,并没有禁止说“猪”字啊,为何有些地区的穆斯林,提到猪的时候要用“黑子”、“壮肉”来代指呢?宗教禁止吃猪肉,可没禁止吃馄饨啊,何况我们吃的是羊肉馄饨,为啥要用“荷叶面”、“元宝汤”来代指呢?
很好理解,这是因为穆斯林们把宗教禁忌扩大化了,弄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禁忌文化。以猪为例,本来古兰经只禁止吃猪肉,信了教之后远离这种东西就是了。远离得久了,情感上对猪这种东西产生了排斥,不但不愿意吃它,也不愿意提它。万不得已要提到猪的时候,就开始用“黑子”、“壮肉”这类词汇来委婉地表达出来。于是,从饮食的禁忌,发展到了语言的禁忌。这种禁忌愈演愈烈,发展到最后,自己不说,也不允许别人说,从卖猪肉的跟前经过,都要屏住呼吸。同学舍友谁敢在我面前提一个猪字,我就恨不得和谁拼命。谁要是在微信里发个猪的图片,那简直就是在制造辱教事件。
由于中国是个汉人国家,大部分汉人是不信教的,久而久之,“汉人”就成了不信教者的代名词,刻意地与不信教者保持区别,也被人引申成与汉人保持区别,尤其是自己本来就是汉人,说汉语,姓汉姓,信了回教之后,更要强调这种区别。否则,万一被人误解成“汉人”怎么办?越是什么就越怕什么,汉地穆斯林最怕你给他头上“扣上”汉人两个字,为了强调自己不是“汉人”,于是各种和汉人有关的东西都有可能遭到抵制,甚至有人处处和汉人拧着来,反着干,以至于逢汉必反。
凡是咱们禁忌的,而汉人没有禁忌的,我们都要树立区别。从猪的禁忌衍生到各个领域的禁忌,别人叫猪,我们叫黑子。别人叫猪肉,我们叫壮肉。既然猪肉的称呼和别人有所不同了,那么猪肉的衍生物是否也得有所区别呢?别人叫馄饨,如果我也去买馄饨,岂不是会被别人误以为我买的猪肉馄饨?所以,我买的是荷叶面、元宝汤。再接下来,猪肉很肥,如果我也爱吃肥肉,岂不是被人笑话,误以为我爱吃猪肉?所以我要把肥字改成壮字,小孩长得肥,也得说长得壮。同样,别人卖肉,往往卖的是猪肉,如果我也卖肉,岂不是要被误会成卖猪肉?所以,即使我卖肉,我也要说成卖菜,卖牛肉要说卖牛菜。这还算好的,如果你万一不幸生在猪年怎么办,有办法,属猪的要说成属亥的,或者属黑的,这就避免了尴尬。
这种禁忌文化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讲究。在西安,爸爸要叫“巴巴”,爷爷要叫“爸爸”,“我爷爷死了”要说成“饿爸爸殁了”,如果你不注意而说成了“爷爷死了”,他们就会哄堂大笑。在河南,有人问你是不是盐丁,如果你一头雾水,回答不是,同样会遭到当地人的耻笑。还有的人,见了面竖起食指,一脸诡异地打着哑谜拷问你这是什么,如果你回答是食指,他们就会一脸轻蔑地认为你没教门,连“伊玛尼”指头都不知道。正如孔乙己嘲笑迅哥,不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一样,各地穆斯林们把他们的禁忌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搞成了秘而不宣的“独门绝学”,稍不留神,就容易踩雷。
很多人把这些无所谓的禁忌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认为是在维护信仰。比如我们称呼真主,如果你称呼上帝,他们就会认为你模仿汉人,是在搞异端外道,其实“真主”二字也是汉语。汉人要贴春联,如果你也要贴春联,他们就会认为你模仿汉人,纵然你的春联上写着歌颂真主的字样都不行,甚至你写的是阿拉伯语,他们也认为不行,如果你说清真寺里不是也有木刻的楹联吗?那不也是对联吗?他们会说,清真寺里是对联,而你贴的是春联。如果你说,春联也是对联啊,春天的对联。我只在春天贴对联,清真寺里一年四季都挂着。如果我有罪,清真寺里的罪岂不更大?他们说,清真寺里是木刻的,而你是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就是模仿汉人,尤其是你用了象征着吉庆的红纸。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由起初的忌讳过春节,发展到忌讳贴春联,再有忌讳贴春联,发展到忌讳一切写在红纸上的东西。
正如阿Q是个秃子,起初只是忌讳别人说他秃,后来忌讳“癞”、“光”、“灯泡”等一切和秃子有关、甚至会让人联想到秃子的事物。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在阿Q看来,这都是关乎着自己名誉的大事。所以,有人要拿这些禁忌取笑阿Q,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被阿Q打,要么阿Q被打。
同样,很多穆斯林有着和阿Q一样的玻璃心,别人稍有不慎,在穆斯林面前提到个猪字,就有可能遭到一顿炮轰,如果再有提着猪肉路过回民区的,则有可能被打得满地找牙。西宁某蛋糕房,因为混进去了不清真的食品,结果遭到群体抵制,宣传资料上写着“他们的行为又一次肆无忌惮地碰触了穆斯林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这句话,真是入木三分。
当今的穆斯林,正是用自己这颗“敏感而脆弱的”玻璃心给自己和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他们用这道高墙,把普世的宗教弄成了奇异的“民族风俗”,他们忘记了宣教,忘记了发展,只顾着在高墙内自娱自乐,洋洋自得。
无花果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打赏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