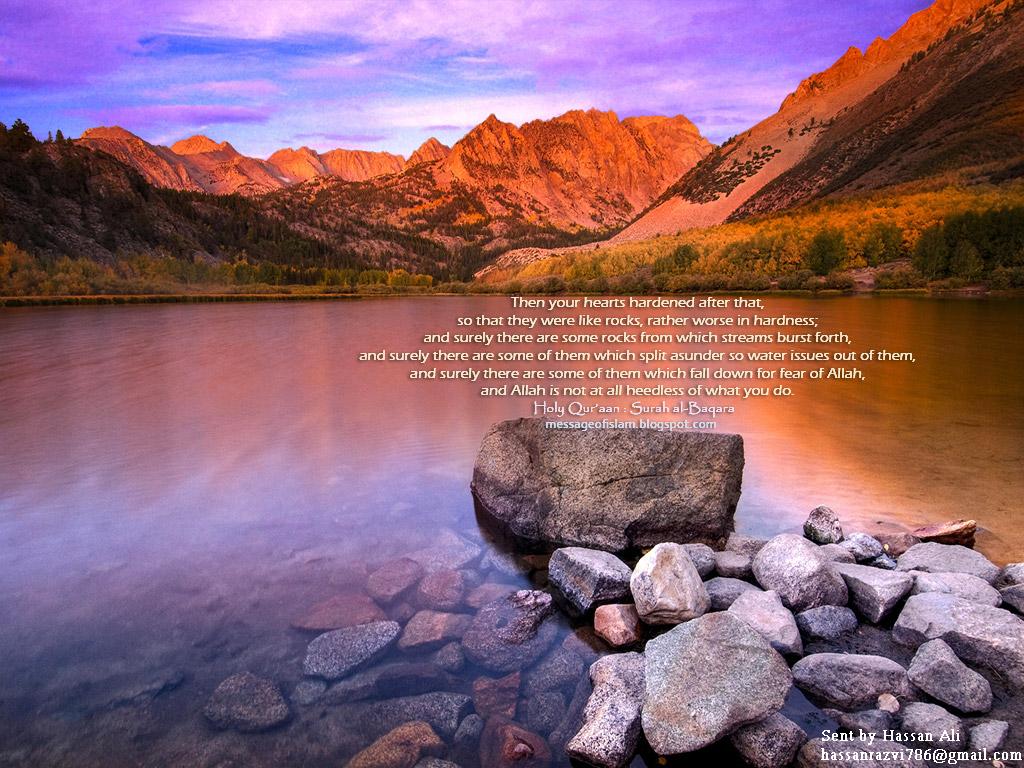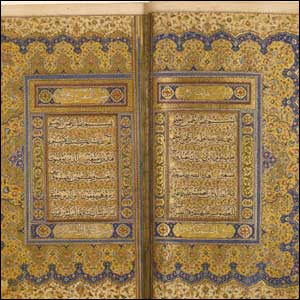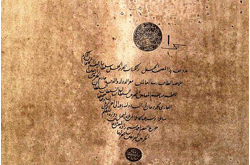晨礼结束,天色蒙蒙,我终于在熬了一个通宵后倒在床上,关闭了手机,准备忘掉一切,好好睡上一觉,哪知道你却走入我的梦中。
音乐响起,你们在欢快地跳舞,非要拉我加入你们的队伍,我连忙拒绝,怕再次被你们嘲笑。要知道我有文学天赋,我有语言天赋,我有音乐天赋,而唯独没有的,是舞蹈天赋。别说你们的舞蹈,就是大学时代的三步四步我也学不会,总是不小心踩住女生的脚,从那之后,我就放弃了任何一种舞蹈的尝试。
你们不以为然,说非常好学,让我站在你们的旁边,把动作分解开来,伸开双臂,翻转手腕,打起响指,两脚要交错前行,我笨拙地模仿,竟然真的学会了,连旁边的古丽也称赞我学得很快,这让我激动不已。
跳了一阵子,你来到我的面前,穿着一件足球衫,下身却裹着一件马来人的纱笼,你浓浓的眉毛,眼眶深陷,因为你们有欧罗巴血统,所以与我们长相迥异。你长长的睫毛,目光依然深邃,只是脸上有了皱纹,毕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你也到了不惑之年。但你的胡子刮得精光,你自我解嘲,说我们这个地方嘛,男人嘛,现在都这样了。
我很惊讶你怎么能来到这里,打算在这里发展吗?家里还好吗?怎么安顿了?你面露难色,我也就明白了七八成。我了解你们的一切,只是学不会你们的舞蹈。你说不是的,你不会了解。怎么不会?我以前以为你们学阿语更容易,发音比我们标准,你曾经纠正过我,说你们的元音发得太轻,以至于把穆罕默德念成了买买提。这让我对你们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你们的语言用阿拉伯字母,我很快掌握了拼读方法,在你们面前结结巴巴地读过,你们也不止一次地给我纠正。我爱听你们的音乐,我翻录了很多盘磁带,用录音机播放。我永远难忘那个彪形大汉,在那个深受不见五指的夜晚,在我面前唱起忧伤的歌。尽管过去多年,但那歌声时常在我耳边萦绕不断,虽然我听不懂那首歌的内容。
关于你们,我知道很多认知都是错误的,我曾一直纳闷,你们的女人为何戴着四角小花帽,露出那么多条小辫子,你们曾告诉我,那都是电视上的,那都是演员,现实中,她们也戴着头巾。然而,这能怪我吗?我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也只有这些。除此之外,我们听不到你们的任何声音。
你的妻子还好吗?那年你俩念了尼卡,你的个子足足比她高一头,但她并不怕你,你把她宠上了天,对她惟命是从。你叹了口气,说你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她了。我问她怎么了,你说也就转发过一个卧尔兹链接,有一天晚上,她就被带走了。七岁的女儿吓得抱着妈妈的大腿啼哭,一家人哭成一团。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像吓傻了一样,尿尿都不知道蹲下去,裤子湿成一片。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还在喃喃地诉说,他说他一家人有六十多口都在里面,他的几个阿卡,连她七十多岁的阿娜。阿娜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学习什么?他轻蔑地笑了笑,学习?我现在只祈祷她能活着。她身体不是还好吗?是的,但好又怎么样?身强力壮的巴郎子,进去的当天,一鞭子打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每次叫他出去,他的手脚就开始哆嗦,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为什么要毒打他呢?因为他通背了古兰经。
能活下去就是好的,能容纳七八个人的房间,一下子塞进去几十人,怎么能受得了?倒下的,抬出去就是了。死了的人,家属知道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答案,很多村庄都空了,很多人一家老少都被弄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那么多人在里面,吃什么呢?有清真伙食吗?我的话刚一脱口,就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一切尊严都没有了,还会尊重你的饮食习惯?想必在里面被迫吃猪肉都是在所难免的。猪肉?他说,哪里有什么猪肉?那么多人在里面,需要多少吨猪肉?就是你想吃都没有,一大锅饭,能有一小块猪油。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十分镇定,而我的心口却越发堵得厉害。我无法想象他们遭受了何种的屈辱和苦难?我也不敢再问。他现在已经妻离子散,我不忍心再勾起他痛苦的回忆。于是我不住地安慰他,希望他能从痛苦之中走出。他的适应能力应该很强,很快就穿上了马来服装了。你喜欢穿着纱笼吗?他说,是啊,我的伤口还没有好,长时间坐着,大家的臀部都生了褥疮,穿裤子的话,血肉模糊,说着他撩起了纱笼的边缘,我看到他踝骨上疤痕累累,而且缝了长长的两道口子。
一股悲愤冲上心头,泪水也涌出了我的眼眶,突然,我从梦中醒来,内心狂跳不止,原来只是一场噩梦。既然是梦,何必当真,我安慰着自己,迷迷糊糊翻了个身,想接着继续睡,然而,他似乎还在我耳边诉说,半梦半醒之间,我不知道这是现实,还是梦境。我知道那年,他们封斋的时候,要把窗帘拉得严严的,不敢开灯,也不敢穿鞋,更不敢开火做饭,在黑夜中默默吃着干粮。我知道那年,他们把家里的古兰经,连同所有宗教书籍,都付之一炬,边烧边哭。有的人怕烟雾引起怀疑,就把经书扔进河里,我知道那年,古兰经在河里堆积如山,顺着河水缓缓流到了边境。我知道他们不能留胡子,不能戴头巾,我知道他们从微信上一个个消失,再也没有了下落。然而,我却不知道梦中的事情,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不,不是的,这只是我睡眠不好,毕竟我把白天过成了黑夜,以至于大白天我还在睡觉,所以常常噩梦缠身。但他怎么会走进我的梦里,我把白天过成了黑夜,难道他把黑夜过成了白天?所以他才能穿越那漆黑的夜色,幽然来到我的梦中,与我灵魂相会,来告诉他的遭遇。否则,他插翅难飞,怎么能够来到我的跟前?
他断然是过不来的,这只是一场梦,梦境毕竟是荒诞的,虽然那么触目惊心。那挥舞着的皮鞭,我只在耶稣受难记的电影里见过,现实中怎么会发生。人们被集中的地方,也只在上世纪德国出现,文明社会怎能还会重演?这一切估计都是我的记忆碎片,在脑海中无意识地拼接组合了罢。不可能是他,毕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我也很多年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歌声,后来的我,迷恋上了秦腔,歌舞升平,早已遗忘了冬不拉的曲调,模糊了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再说了,我何曾会跳他们的舞蹈?也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一个动作,现实中,我对他们的舞蹈不感兴趣,除了爱吃他们的拉条子,我对其他的一切都装聋作哑。
然而,梦境却是那么清晰,他那深邃而忧伤的眼神,是那么真真切切,定格在我的脑海,让我再也无法入睡。我不能无视他的出现,继续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又没有任何办法,不能替他呐喊,不能替他鸣冤。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杳无音讯,生死未卜。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无法判断来到我梦中的,是他的真身,还是他的亡魂。但他的到来,使我没有理由继续蒙头大睡,而是让我这尚未泯灭的良知苦苦挣扎。我要把这一切向真主诉说,我知道,在这无边的噩梦中,他是唯一的光明。
万能的真主啊,你俯瞰着我们,求你倾听地上的声音,求你结束我们的噩梦。求你赦免那些无辜的男女,解除他们的灾难,让他们再也没有惊恐,没有哀伤。如果他们活着,求你解救他们摆脱不幸;如果他们死了,求你抚慰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离开这悲惨的世界,安然回到你的身边。
无花果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打赏
-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